金庸作品中,对“侠”概括最好的有两句话,其一是“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其二,《倚天屠龙记》里写道:“怜我世人,忧患实多”。
【东西问客户端9月5日电】“凡有华人处,皆读金庸书”。在华语文学世界里,金庸先生的影响至深至远,他的小说和他小说改编成的影视作品“承包”了几代人的青春。然而,金庸留给后人的绝不仅是娱乐化的通俗阅读,他所塑造的武侠世界本身,就是一部丰富的中国侠客文化史。
金庸笔下,不同的江湖里流淌着相同的侠客精神。中国的侠客精神是如何形成的,与历史文化有何渊源?在金庸武侠里,究竟何为“侠之大者”?东西方作品中对侠客形象的塑造有何异同?知名自媒体人、作家王晓磊(六神磊磊)近日接受中新社旗下“东西问客户端”专访,对此做出深度解答。
记者:在中国,从荆轲刺秦开始,就已有了侠客的故事和对侠客的描述。中国侠客文化的源头是什么,其发展脉络是怎样的?中国历史及传统文化与侠客文化的渊源有哪些?
王晓磊:武侠以“侠”为主,它若只有“武”也不会有人看。侠有正义感、除暴安良、能反映民间诉求,所以武侠的核心是“侠”。中国有数千年文化史,侠的文化也有几千年,源流非常长。一般认为,侠文化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先秦以前,《史记》里有《刺客列传》,其中提到的刺客就是侠。他们有侠气,但那个时候,“侠”精神的内核是忠诚,不强调太多正义感,而是忠于主人、忠于君上。唐朝出现了传奇小说,描写了许多极其打动人的侠客形象,如聂隐娘、虬髯客。到了明清,关于侠客的故事和小说越来越多,众所周知的《三侠五义》《水浒传》,那是侠客精神、侠客文学比较繁荣的时期。上个世纪,新派武侠小说诞生,从而出现了金庸、古龙等诸多大师。
陈平原先生说:“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国文化里一直有“侠”的精神。不妨以诗歌举例,一个看似最“不侠”的诗人——陶渊明,他也写诗《咏荆轲》,写到易水送别时称“渐离击悲筑,宋意唱高声”,这一刻,他都幻想自己提着宝剑去做侠客。唐朝诗人十有六七有侠客情怀,特别是李白。直到今天,有关李白的绘画、雕塑,出现概率最高的是酒,第二高的是剑。杜甫给人感觉和“侠”不沾边,但他的诗里一样饱含很多侠客元素: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再者,人们提到中国文学往往想到“四大名著”,《水浒传》就是侠义小说,《三国演义》、《西游记》里也有很多侠客精神,哪怕《红楼梦》,同样有侠的色彩,塑造了“醉金刚”倪二、柳湘莲这样的人物。如果没有“侠”文化,四大名著要少一部到两部。所以说,侠文化在中国文化发展脉络中是贯穿始终的。
记者:“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是出现在金庸小说中让很多人豪气顿生的金句。在江湖恩怨和儿女情长的纠葛中,拥有大德、大义和大担当的“家国情怀”,才配得上一个“侠”字。你如何看待金庸对“侠”的这一理解?
王晓磊:金庸先生生在一个动荡的中国,读书时正赶上日本侵略,少年的他见证了民族的苦难史,这些经历在他心里种下了“侠”的种子,并将其带到了日后的创作和对“侠”的理解中。在他看来,一个侠之大者必须有家国情怀,这与他自身经历有关。
在我看来,金庸的“侠”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社会责任。家国情怀、为国为民都是社会责任,一个人有能力就要为社会的美好与和平尽到责任,典型人物如郭靖。第二个层面,个人修养。侠客要追求个性的解放,从而实现人生价值。
金庸作品中,对“侠”概括最好的有两句话,其一是“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是一句特别重要的话,是他自己提炼出的“侠”的精神和内涵。其二,《倚天屠龙记》里写道:“怜我世人,忧患实多”。这句话的本质是同情、是悲悯。所以,金庸笔下侠客的首要人格是责任感与同情心。
记者:你从一个“金庸迷”到一个沉浸在武侠世界里的研究者,侠义精神的内涵也在变化中发展,当代社会如何理解武侠精神?
王晓磊:当代法治社会中,武侠肯定没有字面意思上的“武”了,但“侠”仍有时代意义。责任感和同情心,这种内涵是不会过时且可以传承的,今天的社会依然呼唤这两种精神。回顾金庸小说中的大侠,倘若没有这两种精神一样可以活得很好,比如乔峰。他在宋朝待不下去到辽国去,身居高位、手握重兵、潇洒肆意,但正因为始终怀有对世人的责任与同情,所以他选择那样的结局,成为一个悲剧英雄,这种精神以今天的价值观看,依然可贵。
“武”则演变出了新的时代意义。“武”在今天的表现首先应该是“不畏惧”,对磨难和未知的“不畏惧”。其次是提升自己。对当今社会而言,强身健体也好、学习知识也罢,无止境地提升自己可以表现在各个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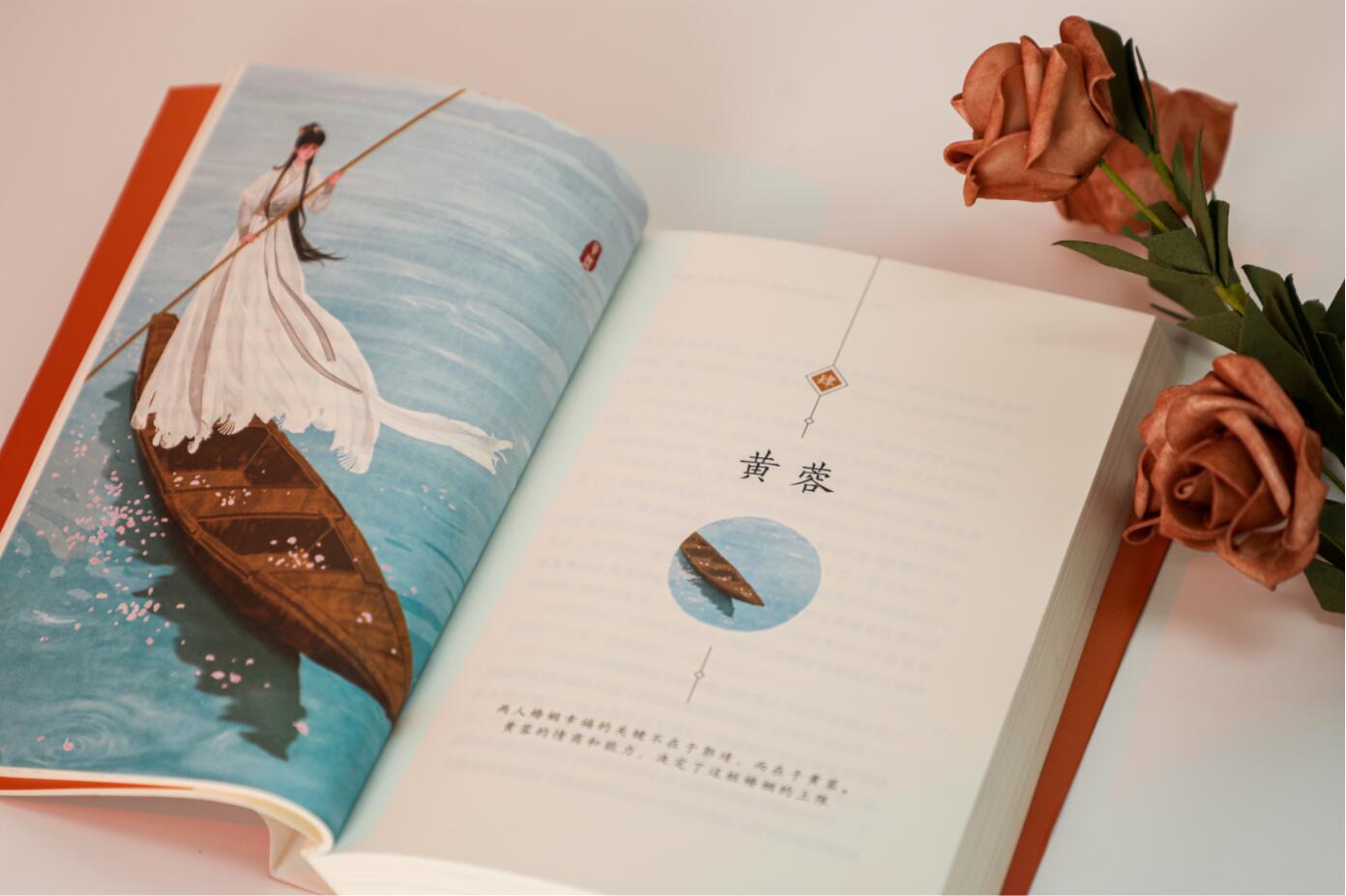 ▲六神磊磊新作《越过人生的刀锋——金庸女子图鉴》插画。
▲六神磊磊新作《越过人生的刀锋——金庸女子图鉴》插画。
记者:纵向上来说,中国侠文化从古至今一脉相承。横向来看,就东西方社会而言,侠文化是很多文学作品的母题。东西方作品里“侠”的形象及内涵理念有何异同?
王晓磊:东西方都有侠,且东西方的侠客文学都被大众喜欢。不同的是,西方的侠,战士也好、骑士也罢往往是社会的上层或中上层,骑士不是平民就可以做的。但是,中国的侠客大多是社会的中下层、是平民。先秦两汉出现的侠客,他们的职业往往是引车卖浆者,是看大门的、杀猪卖肉的,他们往往为了报恩去行侠,但最后的归宿还是平民。纵观整个中国文学里的侠客,很少有人为了提升社会阶层、为做重臣而行侠仗义,他们来自江湖、最后也隐于江湖。
此外,西方文学里的侠是有一套制度来匹配的,其中包括享受的待遇,获得的头衔、名号、爵位,以及如何分级、如何晋升。中国没有有关侠客的制度,这些人没有编制。我们想到侠客首先映入脑海的画面是小酒馆、小客栈,是游荡在塞外边关、漠北江南,但这些人却怀着热血做着特别正义的事。
为何东西方侠客会有此不同,原因涉及历史和文化等各个方面,但有两点最有意思。侠客形象大多来自于文人的书写和塑造。文人自己不能武,“侠”是他们无法实现安邦定国的志向,或是在理想不可得的情况下的另一个投影——投身江湖行侠仗义。所以,中国侠客的“边缘”其实是文人的落寞,这也是“千古文人侠客梦”的原因之一。
另外,还是跟中国古代制度有关。数千年来,侠客像一把双刃剑,在古代多数时期的社会里,侠客是不被制度接受的。侠客只在春秋战国时被允许公开征募,被短暂地推崇过。秦汉以后,司马迁《游侠列传》里写到的侠客,最终都逃不过被制度打击和抑制的命运。因此,他们注定“边缘”,自己流放自己。
东西方作品里的侠客也有共同点,西方侠客也强调社会责任、除暴安良,他们也会为了族群、领地、人民和国家,甚至为了爱情行侠客之事、奉献自己的人生。
记者:金庸先生坦承,在武侠世界里,男子的责任和感情是仁义为先的。但“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故事中的女子形象,如何不输“侠”气?
王晓磊:这是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中国古代文学名著里,女性角色很少,基本是陪衬或是“工具人”。“四大名著”只有《红楼梦》认真写了女性。但有趣的是,女性在古典侠义小说里的地位却很高。著名古代版画《三十三剑客图》选了《唐宋传奇》里的三十三个知名剑客,其中有1/3是女性,最出彩的人物也基本是女性,比如赵处女、聂隐娘、红线。
女性明明是弱者,为何会在侠义小说里如此亮眼?
首先,可能因为女性往往敢爱敢恨。爱恨的关口女性拿得定、豁得出、用情深。其次,女性更富有同情心。富有同情心又敢爱敢恨,天然的就有了侠的底色和胆气。所以古代关于女侠的故事非常多,金庸先生写的《越女剑》,就是一个塑造女侠的故事。很多人好讲天道、王道、霸道,金庸先生,一个写武侠小说的人反而好讲人道,而他笔下的“人道”里,女子被放在了一个平等的位置上,她们的侠气从未输给男儿。(完)
作者/陶思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