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代刻石是探寻那一时期历史的重要载体,不仅受到国内学者的重视,也引起了海外汉学界的广泛关注。
从今年6月起,青海玛多县扎陵湖北岸发现的一处刻石,在学界掀起一场近年来少有的公开学术争鸣。一时间,刻石时间真伪之辩,刻石内容释读之辩,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各抒己见。
9月15日,国家文物局发布消息,认定该石刻是我国目前已知唯一存于原址且海拔最高的秦代刻石,并定名为“尕日塘秦刻石”。

▲尕日塘秦刻石资料照片。(中国国家文物局供中新社)
刻石记载了什么内容?据介绍,尕日塘秦刻石的文字刻凿壁面总长82厘米,最宽处33厘米。刻石全文共12行36字,外加合文1字,共37字,文字风格属秦篆。国家文物局发布了对石刻的释读结果,保存较完整的文字信息为“皇帝/使五/大夫臣□/將方□/采樂□/陯翳以/卅七年三月/己卯車到/此翳□/前□可/□百五十/里”。大意为:秦始皇派五大夫翳率方技家去昆仑采药,翳乘坐秦始皇三十七年三月己卯日的车到达此地。
这是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的重要成果,与扎陵湖关联形成文化景观,整体保存基本完好,文字多数清晰可辨,刻石中年月日俱全,不见于文献记载,是中国目前已知唯一存于原址且海拔最高的秦代刻石,矗立河源,补史之缺,意义重大,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
秦代刻石是探寻那一时期历史的重要载体,不仅受到国内学者的重视,也引起了海外汉学界的广泛关注。其中,被誉为“全才”的法国著名汉学家沙畹,便在这一领域进行了深入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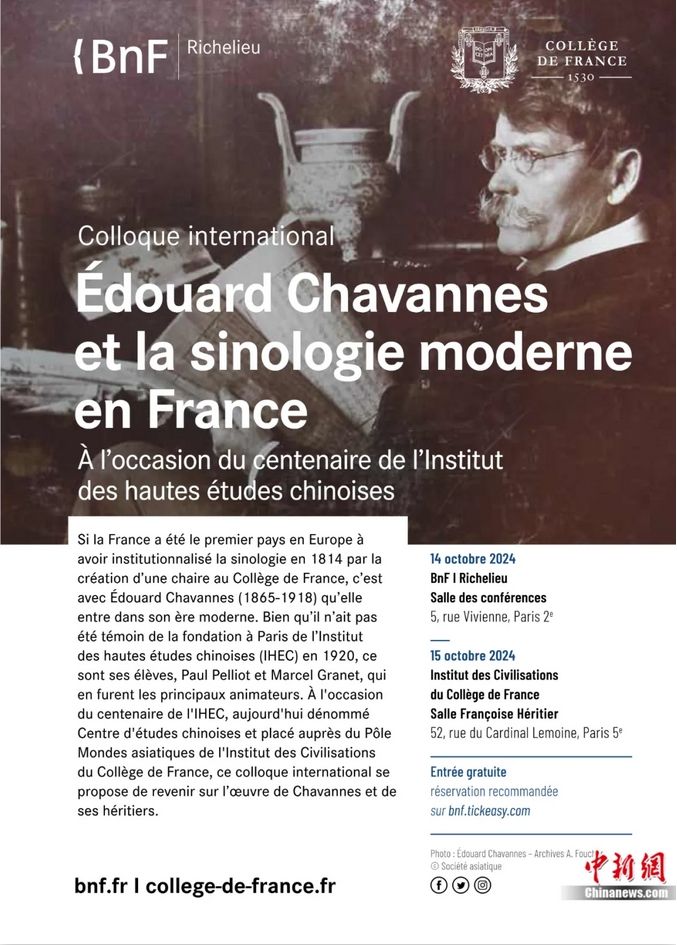
▲“沙畹与法国现代汉学”学术研讨会海报。(图片来自中新社)
沙畹的碑铭学研究起源于《史记》的翻译和研究。在研读《史记·秦始皇本纪》时,沙畹注意到司马迁记载的秦代刻石文,这一部分内容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因而在《史记》译注之余又进行了专门研究。与此同时,他也开展了对汉代碑铭的研究。1893年,这两份学术成果在同一年面世,即发表在《亚细亚学报》上近50页的一篇论文《秦碑铭》和在巴黎出版的一本专著《中国两汉石刻》。
在《秦碑铭》一文中,除了引言、结语各一页,其余部分主要是8种碑铭的考证与译文(37页)、碑铭文音韵研究(6页)和秦代瓦刻简介(3页)。沙畹介绍的第一篇石刻文是《诅楚文》,应是战国后期秦惠文王时期(约公元前4世纪)所刻,发现于北宋。值得一提的是,《诅楚文》并未被中国学界归入著名的秦七刻石之列,而沙畹将其纳入秦碑铭研究范围,这说明他以一种更具历史观和发展观的角度来看待问题,把秦看作一个存在历史更长的政治实体,而不局限于历史短暂的秦朝。
沙畹在研究每一种秦刻石文的时候都进行了细致的形式分析。尽管在《史记》或其他金石文志中,刻石文显示为散文体排列,但是沙畹对其内在的节奏和韵律十分敏感。例如,他认为峄山刻文由36句四言组成,每3句一组,形成一个12字的诗行。在介绍琅琊刻石文时,沙畹指出了其在节奏上的独特之处,即第一部分为整饬的72句四言,而第二部分则不够规律,有骈散结合的特点。
可以看出,沙畹的秦刻石文研究是非常全面和系统的,不仅重视历史考证,而且关注形式格律。在他看来,“秦朝虽短,但却是中国古代为后人留下最为可观的刻石文物的朝代”。他对秦刻石文的翻译与研究与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也是相互衔接和融会贯通的。他本人非常重视中国文学研究,1893年12月5日在法兰西公学院的汉学讲座第一讲便以“中国文学的社会角色”为题,其中说道:“中国文学传播之广,延续之久,在思想各领域及生活各方面影响之大,使之成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导师。如果想认识并了解如此富有生命力的文明,就必须学习中国文学。”
参考中新社、《汉学研究》杂志、《光明日报》、《中国新闻周刊》等内容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