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学作为20世纪哲学的一个重要流派,始于胡塞尔的思想,并在海德格尔、梅洛·庞蒂以及萨特等人的发展下,形成了丰富的理论体系。
现象学作为20世纪哲学的一个重要流派,始于胡塞尔(Edmund Husserl)的思想,并在海德格尔、梅洛·庞蒂以及萨特等人的发展下,形成了丰富的理论体系。其核心理念是“意向性”(Intentionality),即意识总是指向某一对象,探索个体如何感知世界,并通过这种感知塑造其生活经验。现象学不仅在哲学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文学批评提供了新的方法论框架。通过“现象的还原”这一核心技术,现象学呼吁研究者回到直接经验的层面,剖析文学作品中人物的内心世界、感知过程和情感波动。在文学研究中,现象学的视角能够揭示出作品中人物的深层心理及其与世界、社会、历史的复杂关系,提供了对经典文学作品更加细致入微的理解。本文将探讨现象学在外国经典文学研究中的应用与启示,特别是如何通过现象学的框架分析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体验、感知与情感,进而揭示其深层的社会文化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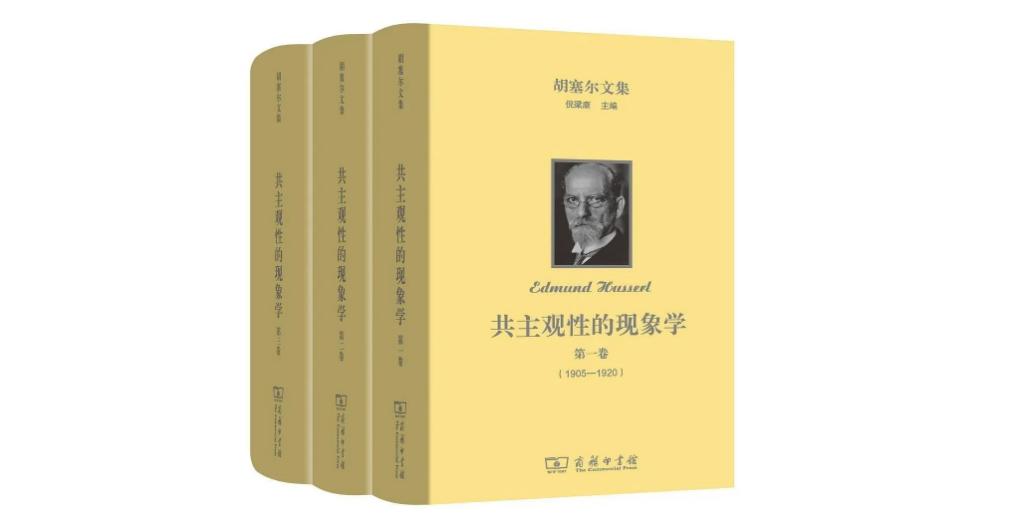
▲《共主观性的现象学》书封。商务印书馆,2018年11月。
现象学强调意识的“意向性”——从人物内心出发
现象学的核心概念之一是“意向性”(Intentionality),即意识总是指向某一对象。意识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总是与外部世界的事物发生联系。这意味着,人类的感知和经验始终是有目的的,意识的活动是指向具体的对象或现象的。在文学作品中,人物的意识、感知和情感是文学创作的核心要素。现象学将“意向性”应用到文学批评中,可以帮助批评者更深入地理解人物的内心世界,揭示人物的感知和情感如何塑造他们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例如,普鲁斯特的叙事方式打破了传统小说的时间顺序,通过碎片化的记忆和感官体验重构了主人公的生命历史。“意向性”概念在他的小说《追忆似水年华》中得到了充分体现。马塞尔的回忆并非单纯的时间流逝的记录,而是由他的意识所构建的一个个瞬间,充满了感官体验的细节。特别是“玛德琳饼干的味道”这一细节,成为小说中的关键转折点,通过这一感官经验,马塞尔重新进入了他与母亲、祖母以及社会的关系中。通过现象学的还原,可以看到,普鲁斯特所描写的“记忆”并非对过去的机械回忆,而是意识对过往经验的再建构。这种记忆的重建过程中,时间不再是线性的,而是由意识对感知和经验的重塑所构成。这种回忆不仅仅是对过去的简单回顾,而是一种对“生活世界”的深刻重建,反映了人物如何通过感知和记忆与外部世界建立联系。通过现象学的视角,批评家不仅关注事件本身的发生,而是关注马塞尔如何在情感和感知的层面与外部世界互动。意向性帮助读者理解人物如何在不断变化的感官体验中寻找意义,如何通过个体的意识活动重建他们的生活经验。
现象学中的“生活世界”——文学中的个体经验与社会背景
现象学还提出了“生活世界”(Lebenswelt)这一概念,强调个体的意识不仅仅是内心的活动,而是与他们的日常生活、社会关系和文化背景紧密相连。生活世界是个体经验的基础,是所有感知、行动和交往的场所。对于文学作品来说,人物的行为和情感不仅反映了他们的个体意识,还与他们的社会背景、历史情境密切相关。在文学批评中,现象学的“生活世界”鼓励批评家深入探讨人物如何在社会、历史和文化的框架内感知和构建他们的现实世界。
例如,在卡夫卡的《变形记》中,故事中的主人公格雷戈尔·萨姆萨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巨大的昆虫。他的变形不仅是个人的生理变化,更是他与家庭、社会、甚至自我认同之间断裂的象征。格雷戈尔的内心世界充满了自我疏离感和对家人关系的紧张,他的“生活世界”因此变得越来越封闭和孤立。格雷戈尔的变形其实是他与外部世界之间日益疏远的表现。他逐渐失去了与家庭成员的情感联系,也在社会中失去了作为“正常人”的身份。这一变形过程揭示了现代社会中个体如何面临自我认同的危机,以及他们如何在社会压迫和家庭矛盾中迷失自我。通过窥探格雷戈尔的“生活世界”,读者也同步感受了他的意识与感知过程。格雷戈尔的疏离感和孤独感并非突如其来的,而是在长期的家庭关系和社会角色压力下逐渐积累的结果。他的变形更是他内心世界与社会背景之间冲突的具象化表现。在这一层面,“生活世界”的概念为文学批评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背景视角,帮助批评者理解个体经验与社会、历史、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使得批评者能够把文学作品中的人物行为、情感和思想放在更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进行解读,而不仅仅局限于个体层面的心理分析。
现象学的“还原”方法——回归直接体验,揭示隐藏的意义
现象学的“还原”方法,或称“现象的还原”(Phenomenological Reduction),是现象学分析中非常核心的技术之一,它要求暂时放下所有的预设观念、理论框架和解释模式,回到事物最原始、最直接的经验层面,以便从体验和感知的角度重新理解个体如何构建和理解世界。在文学批评中,现象学的“还原”方法可以通过人物的意识流动、感知、情感和记忆来理解作品中的人物所经历的巨大内心变化与感情冲突,进而揭示出他们内心的世界和他们与外部现实的关系。
在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这一复杂的史诗作品中,现象学的“还原”方法提供了一种非常有力的解读视角,能够揭示出小说中的人物如何通过直接体验感知战争、家庭、爱情、死亡等重大主题,并呈现出他们在历史和社会环境中的心理变化和情感波动。例如,皮埃尔·别祖霍夫在战争中的经历,尤其是在博罗季诺战役中的体验,可以通过现象学“还原”来进行分析。作为一个具有深厚哲学兴趣的角色,皮埃尔在战争中并非仅仅是作为一个战士参与,而是通过独特的意识状态、对死亡的恐惧、对生活意义的反思以及与他人的关系的感知,来重新认识自己与历史、社会和家庭的关系。通过现象学“还原”,学者不仅关注皮埃尔在战场上的行为,还要关注他如何在生死边缘、在血腥和混乱中感知自己的存在,如何在这些感知的过程中重新定义“生活”和“意义”。这种分析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皮埃尔为何在战后经历了深刻的内心转变,最终回归对家庭和社会的责任感。
现象学的“还原”方法可以在文学作品中深刻分析人物的内心世界、感知过程、情感变化及其与历史和社会的关系。通过“还原”回到人物最直接的体验层面,关注他们如何感知自己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以及这些感知如何塑造他们的思想、行为和人生轨迹。现象学的视角能够更细腻地解读托尔斯泰笔下人物的复杂心理和情感波动,并帮助理解他们如何在巨大的历史背景中寻找自我和意义。
现象学的情感体验分析——揭示人物心理的深层结构
现象学不仅关注感知和意识,还特别重视情感体验。现象学派认为,情感并非孤立的,而是与人物的意识结构、他们对世界的感知密切相关。通过对情感体验的分析,人物的情感如何通过意识的流动逐步展开并影响他们的行为和决策得以显现。在文学作品中,情感是塑造人物行为和决策的关键因素。现象学的视角为学者提供了一种分析人物情感的独特方法,探讨情感是如何在人物的意识中浮现、变化和表达的。
首先,个体的内心体验随着感知和情感的流动会不断变化。在《包法利夫人》中,艾玛的情感并不是固定的,而是充满了波动和转变。从最初的幸福、激动到后来的失望、空虚,再到最终的绝望和死亡,艾玛的情感经历了复杂的流动性和变化。这种情感波动反映了她内心世界的深刻不安和对自我身份的迷茫。“情感的流动性”概念让读者可以理解艾玛的情感如何在不同的时刻、情境下发生变化,揭示出她对理想与现实之间差距的痛苦体验。她的内心充满了矛盾:她渴望爱情与自由,但又无法真正摆脱婚姻和社会角色的束缚。此外,现象学通过“还原”个体的体验揭示其背后隐藏的“本质”或结构。艾玛的情感不仅仅是对爱与激情的表面渴望,更是她寻求自我认同的内在驱动力,是一种寻找自我、重塑自我形象的方式。她的情感与她内心对“理想自我”的追求密切相关,认为只有通过非凡的爱情和远离日常生活的冒险才能实现个人的价值与独立。她认为自己应当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女性,而不是局限于家庭主妇的角色。然而,她无法通过这种方式找到真正的自我,反而将自己陷入了更深的情感迷茫和失落。她的情感经验反映了她对“本质”认同的失败,这种失败最终导致了她的悲剧。
小结
现象学作为一种批评方法和视角为文学研究提供了独特的启示,它强调通过还原和分析个体的直接经验,尤其是情感、感知和意识的流动,来揭示文学作品中人物的内心世界及其与外部现实的互动。现象学注重的是个体如何在特定情境下感知和构建自己的生活世界,它关注人物在日常生活和极端情境中的情感体验、意识变化以及自我认知的过程。因此,现象学的批评方法要求研究者深入到人物的主观经验中,关注他们如何通过意识的“意向性”将外部世界内化为个人的情感和思想,从而揭示出人物情感背后的深层动因和社会文化背景。
通过现象学的视角,研究者能够打破传统文学分析中对外部行为和情节的简单解读,更加关注人物与世界之间微妙的互动过程,探讨他们如何在不断变化的情感流动中重构自我。现象学分析不仅关心人物的行为和语言,还探讨他们在不同时间、不同情境下如何通过感知和记忆重建过去、塑造现在、预测未来,从而形成复杂的心理结构和情感轨迹。此外,现象学批评还可以帮助揭示人物的意识如何在多重社会角色、历史背景和文化价值观的冲突中产生张力,如何通过与他人的互动、与社会的碰撞以及与自我认知的对话来实现自我认同的建构或解构。
总之,现象学的批评方法为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更加细腻、复杂和多维的解读方式,它要求研究者关注文本中人物的内心世界与外部现实的交织,探索情感、意识与经验如何在文学作品中交相辉映,最终揭示出作品深层的意义与人类经验的普遍性。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人物如何在社会和历史的背景下,凭借个体的感知和情感构建他们的生命意义和存在状态,从而为文学的解读提供更为深刻的视角。(完)
(作者/谭源星,成都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